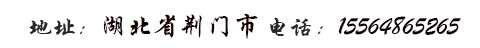评论朱彤弋舟小说的辩证法
|
儿童白癜风怎么引起的原因 http://m.39.net/pf/a_4354379.html文章来源 《山东文学》.5弋舟小说有一层薄雾般的迷人气质。近作《庚子故事集》品相的精致,行文的气韵与腔调,再次印证了他的美学野心。但其小说阐释的难度并不全在于此,更多在于叙事的多种双重性症候——新经验与旧经验、明与暗、轻逸与沉重、虚空与现实、崇高与庸俗、古典与先锋、传统与现代。在这多重辩证之间,层层落落地建构起了独具标识的美学风格。一、“轻逸”: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在古希腊神话中,蛇发女妖美杜莎的目光拥有石化他人的能力,伯尔修斯穿着飞行鞋,乘着风和云,以铜盾为镜像巧妙地割下了美杜莎的头颅。他避开了自己变成石头的可能,拯救了即将被石化的世界。故事所在的世界布满了灾难与沉重的底色,而伯尔修斯却仅用几个细巧之物——风、云、飞行鞋,以及一面小铜盾镜子,抵御了沉重的世界,带来明朗的希望。卡尔维诺将这归结为一个漂亮的词汇——轻逸。并指出了“轻”在创作实践中的三种表征:一是具有象征意义的“轻”的形象;二是减轻词语的重量。从而使意义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时,变得像词语那样轻微;三是叙述一种思维或心理过程,其中包含着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,或描写高度抽象。弋舟便具有伯尔修斯般的魔力,《庚子故事集》很好地实践了卡尔维诺的“轻逸”观念。《庚子故事集》写了此刻的困境与生活的沉重,但它更写出了“生活重负的一种反作用力”。这一“反作用力”肢解、细化到文本之内幻化为“轻逸”的品格。也正是“轻逸”酝酿出的美感聚成一股合力,抵御了小说精神内里的晦暗。这大概就是为何弋舟的叙事总能在某一瞬间,或结尾处,让我们骤然地感到如释重负与疏朗明亮的原因。《钟声响起》虽作为《庚子故事集》的代序,却被弋舟处理得充满艺术感觉与轻逸质地。每天准时响起的钟声,是“轻”的象征,是人处于艰难时刻的盼望与根基。“午后,在准点的刹那,在阳光下或者阴霾中,它悠扬响起……钟声浮现,如律动的朝阳,袅袅跃出往昔被如麻一般纷乱的声量注满了的时空。”“阳光”“阴霾”“朝阳”等具有象征意义的“轻”的形象,以及“悠扬的”“律动的”“袅袅”“跃”等词汇,本身就是轻盈的元素。这与《人类的算法》中“钟声响起”的场景遥相呼应——刘宁被氤氲在黄昏里的钟声所感动:“黄昏中市政厅古老的建筑物披着霞光,突然之间,钟声毫无征兆地响彻天空。她觉得自己被骤然降下的重力击中了,一下一下,不是作用在耳朵里,是直接落在了她的胸口,于是发出了如此的回响……”“黄昏”“霞光”“天空”“钟声”,这些再“轻”不过的意象,却使刘宁感受到了无穷重力。也正是钟声这一介质将她与男孩谭展相连,那隐藏在刘宁心底的一双运动鞋,那捧细碎的胡茬,具备承载往事的沉重与柔情的力量,或许,这些“轻”与“明”可为我们清洗、溶解生活里的“沉”与“暗”。亦如弋舟在小说《平行》中对“老去”意义的描述——原来老去是这么回事:如果幸运的话,你终将变成一只候鸟,与大地平行——就像扑克牌经过魔术师的手,变成了鸽子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《核桃树下金银花》中“金银花”这一植物意象。金银花,正名为忍冬花,小枝细长,中空,枝叶生柔毛和腺毛。正是这看起来微小的平凡植物,却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功效,就像那个胖天使,她在炎炎夏日里为“我”带来的清凉、轻松与柔软。“我”因一个胖天使的出现,更确切的说,是她所描述的那片朴素而浪漫的金银花海的出现,“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,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,变得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,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——变得就像她自己的一身肥肉那样的柔软。”更有意味的是,这一瞬间“轻”的转变,也是通过另一种“轻”,即“跃”上一辆名为“铁马”的电动三轮车来完成的。“彼此换位,跨上去,我觉得车身被我压得向下一矬,那感觉就像是真的跨上了一匹马,它极富灵性地微微下沉,缓冲掉瞬间的重荷之后,又柔韧地挺起了腰背。顿挫之间,简直就是一个活物。”当“我”拖着沉重已久的肉身跨上“铁马”的那一刻,感到了此生从未有过的便利与轻盈。更重要的是,当“我”骑上这匹“铁马”,一头冲向那片金银花海时,不再需要“被教育”,不再必须忍受肉身的重量,重获作为人的最为原始的尊严与自由。再延伸到金银花的物理属性:适应性强,耐寒性强,喜阳,耐阴,耐干旱和水湿,对土壤要求不严。这很契合胖女孩的形象,看似卑微、平凡,却有着极强的适应性与忍耐力。胖女孩是从乡下进入城市的典型代表,她不仅有着沉重的肉身,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“乡巴佬”,是城市的“他者”。胖天使眼里的“全是楼”,与“轻”的乡村中的植物构成了冲突与对比,呈现出一种“进城的失落”。因而,胖天使在汶川地震中的消失,就不仅仅是弋舟刻意植入的历史,它有其注定的悲剧性,以及如何重新审视那些被忽略的人与被遗忘的事物。“核桃树”是另一个植物意象,是经胖天使的指认后“我”此生认得的唯一树木。核桃树的意义不仅在于启蒙了“我”对原野的想象,更在于通过一个“异己之物”来认识自身。小说中存在一个悖论,“我”一旦振作,肉体便开始轻盈,重归消极气馁,肉体便开始沉重。当“我”成长挫败时,只需深夜在核桃树下痛哭一场便会再度振作,进而变得轻盈起来。事实上,核桃树之于只有城市生活经验的“我”来说是陌生的、异己的。但当“我”来到异乡,处于“无根感”时,这棵头顶的核桃树便给予“我”生活下去的力量,在异乡中感受到家的存在。在这一意义上,核桃树和金银花都是“轻”的象征,带给“我”轻盈之感,使“我”获得了一种身份认同。在《鼠辈》中,通篇都被这种“轻与重”的悖论裹挟着。一开篇,“我”便被一只仓鼠体重变胖的故事所吸引,“他的另一半走了,于是,他迅速地膨胀起来。这其实不难理解,他变成了一个胖子。”这成为“我”与那位颇具“仓鼠之美”的女人邂逅的契机。弋舟把这篇小说设计得很巧妙,将“我”、雄性仓鼠“雪糕”、罗宾三者置于同一困境,即被另一半抛弃后体重骤升的境地。罗宾和雌性仓鼠“肉球”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“我”通过女人对“炫灿”的指认走出黑白世界后,如何面对自身面目的改变?小说中有一处细节,当仓鼠雪糕从笼子里溜走而掉进衣柜的缝隙里时,两人仅用“一根鞋带系住一只塑料袋,坠入绝地”,便成功地解救了沉甸甸的它。“一根鞋带”和“一只塑料袋”本是生活中的轻盈之物,不被人所感受与重视,却能使陷入困境之下的仓鼠重见光明。批评家金理认为弋舟的创作有“恢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力”的特质,而这些“具体事物”大多含有“轻”的质素,构成一种飘逸又不失力量的审美感受。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弋舟高度抽象又充满张力的语言:她突然大笑起来,是真的感到了开心,想一想,他们在莱茵河畔的月色下就这么说着杀猪的话题,真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。(《人类的算法》)这当然很残酷,可理解了自己之后,我才能平静地、甚而是不带羞愧地去容忍自己与理解世界。为此,现在,就是此刻,我都能穿着睡裤在三月的春光下轻盈起舞。(《掩面时分》)春夜的风是软的,我在黑暗的天空爬行。爬过十五六米之后,没准,我就能焕然一新,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。(《羊群过境》)城市之夜在一个“炫灿”的指认下,宛如倒挂的宇宙。我的世界就这样被她崭新地定义了。我用自己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。(《鼠辈》)弋舟的语言也是其小说文本“轻逸”的组成部分。“杀猪”话题、“疫情”“城市之夜”与“莱茵河畔的月色”“三月的春光”“春夜的风”“炫灿”等词汇同时凝集在句子之内,充满了叙事张力。同时,这种叙述还充满日常生活的哲学性,充斥着诸多不可感知的元素,高度抽象。在这一意义上,弋舟小说的语言已经逸出了先锋文学的边界,完成了一种创新和超越。语言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那里显出格外的重量,但语词、句式过度的精雕细琢,不仅干预了内容本身,也造成了意义的消解与深度的丧失,叙事也只能沦为一场虚无的游戏。而到了90年代,语言的精致与雕琢却在大部分的先锋作家那里消失了,他们由注重形式转而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hetaorena.com/htrpz/1047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浅析商洛核桃产品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
- 下一篇文章: 手绘板零基础教程,零基础学画先学什么容易